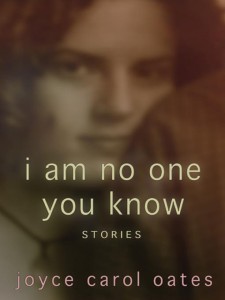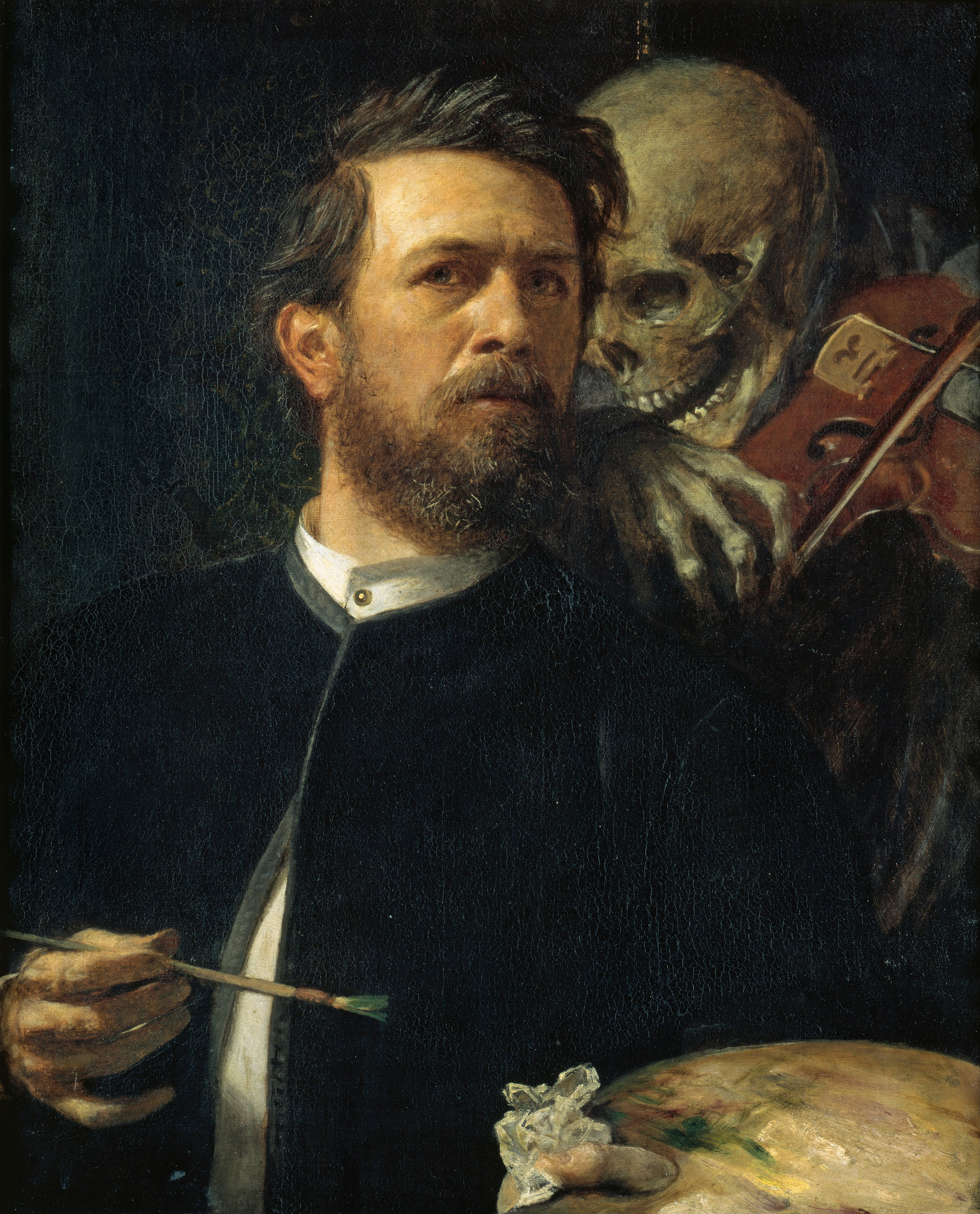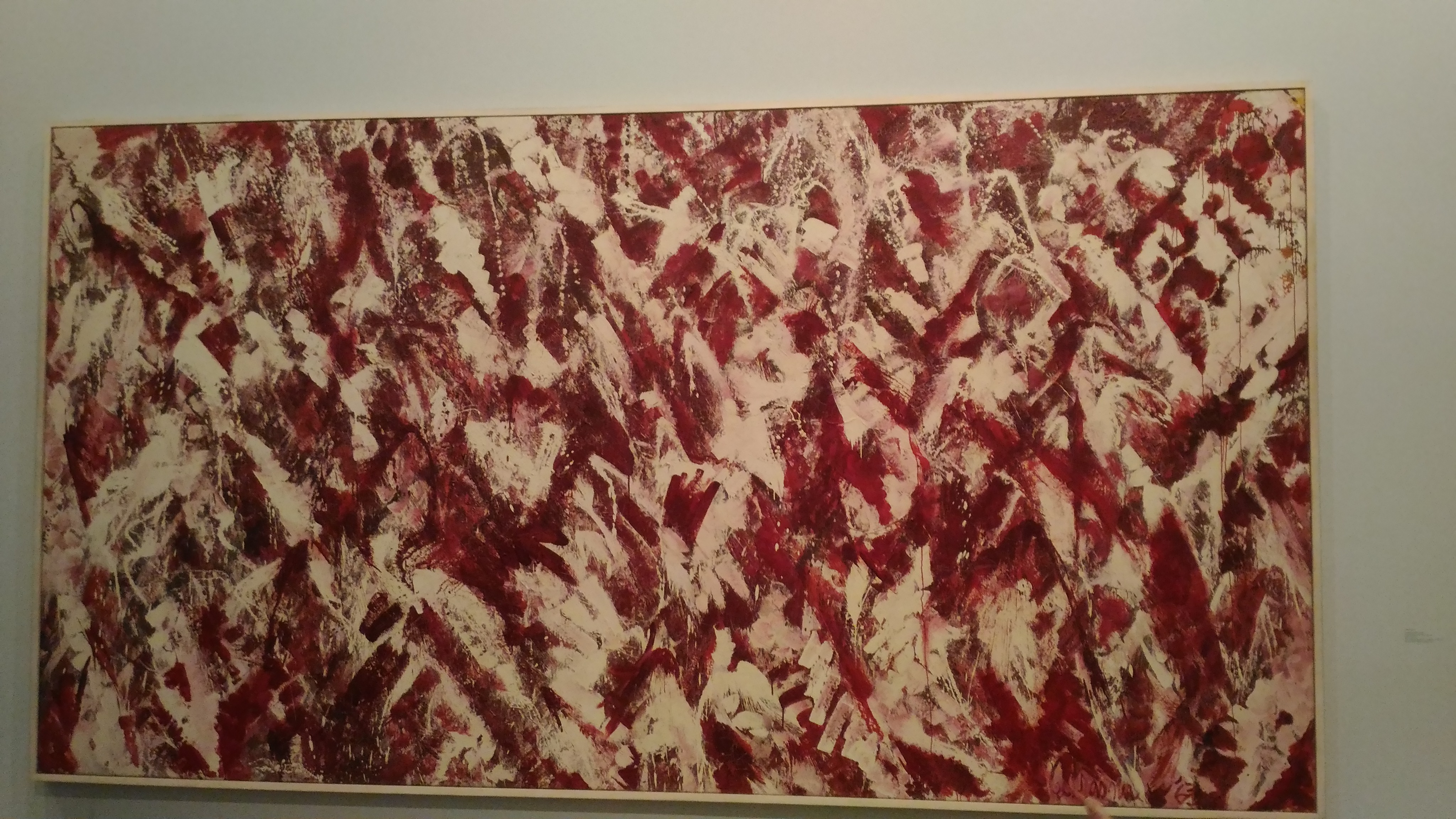最近,為了學習英語,我上New Yorker看英文小說。對於西方文壇,我了解甚少,很多投稿的作家我都不認識,但單純欣賞小說也是好事。
剛看了一篇短篇Jelly and Jack,是我喜歡的小說類型,筆觸細緻,內心描寫飽滿,現實主義手法,不炫技,卻討論很嚴肅的話題。我眼中出色的小說,是以日常生活裡最普通的情節探進人性、社會的肌理,呈現存在的狀態。現代文學的反小說傾向,我不討厭,也不算特別欣賞,很多小說作者寫得晦澀難懂,意象繁複,但未必懂得說故事。小說的基本,不是說故事嗎?我喜歡小說,是因為我想追看情節,享受故事。寫小說我還不算擅長,但我比較想從基本出發,再玩花式,像畢家索創出什麼什麼主義的畫風前,還是從最根本的素描畫畫起。
最近寫了一篇關於死亡的小說,朋友說我寫女主角的心情欠缺層次,由開首到結尾女主角都只有難過和無奈。Jelly and Jack層次鮮明,對我來說是很好的範例。故事發生在1985年,Jelly是個半瞎的中年女子,罹患腦膜災後,她的視力嚴重衰退,需要架上一副厚眼鏡才能應付日常生活。她對自己的外貌和身體失去自信,不敢主動結識異性,就從電話簿裡找來陌生男子的電話,跟他們在電話裡談情,但永遠不跟對方見面。她每天在視障中心當義工後,回到家裡就盤桓於幾位男士的電話之間。她對於電話調情非常熟練,在她與Jack的交談裡,她懂得以共同朋友開展話題,欲拒還迎爭取好感,控制談天的節奏,計算何時沉默,何時給予回應,也為自己定下每逢週日才跟Jack談天,從不逾時,也不把電話交給對方,讓對方對自己有所期待。
Only Sunday, and it would only be her calling him. Parameters. Predictability. That was the way it would work best for both of them, for this thing they were building between them.
Pace was important. She would make him her Sunday call, and, as the weeks of talks went by, he would accept her terms. He would begin to get great pleasure out of counting the days until Sunday.
電話裡的Jelly是情感操控者,她為jack劃下情感陷阱,讓Jack一步一步走進去。但慢慢地,隨著Jack在電話向她打開心扉,談起他與女兒的關係而感觸落淚時,Jelly深受感動,她不再是控制Jack、迷惑Jack的那一位,而是反被Jack吸引,她變得經常跟他談天,還把地址(她的另一個地址)給了他,把自己部分的真實故事告訴他。她感到自己的心與jack很親近,慢慢愛上Jack。然而,當Jack向她表白想跟她約會時,她就猶疑了,徘徊於懷疑自己與Jack的距離太大的矛盾中。
從冷靜的引誘到受吸引不能自控的層次變化裡,我看到女主角的慾望也一層一層加深。起初Jelly打電話給Jack,就如她打給其他男人一樣,是為了 :
She felt like a grad student in the same way that she felt blond and supple and young when she talked to Jack. She felt elegance in her hands and wrists.
這是她建立自信的方法。但建立自信的背後,隱藏著微妙的性慾望。她還是大學生時,曾收過騷擾電話,她雖然憤怒地摔電話,但心裡卻盼望著對方再打來,想像著對方的樣子,認為電話是weapon of intimacy,電話正正勾起她情慾。到現在,如果男友們在電話裡表達出性慾望,Jelly很自制地認為不能到達性的地步,因為她不想要真實的性,她怕自己破壞對方的想像。在認識Jack前,Jelly曾與Mark深交,Mark很想知道她的樣子,她就把美女朋友Lynn的照片寄給他,讓Mark幻想自己是個美女,但當Mark非要約她見面不可,想進一步發展情侶關係時,她的進退兩難使戀情無疾而終。這種對感情迫於無奈的自制,蘊含著無法被滿足的性慾望。當Mark向她表白愛意時,Jelly想像自己披著Lynn的身體而與jack做愛,她的性幻想來於男人對她的想像。
She was herself, but in Lynn’s body. She imagined Mark undressing her and touching her perfect, pink-tipped breasts as they spilled out of her bra, her smooth thighs under her skirt, her supple but taut midsection, her round high ass. She watched her fantasy as if it were a movie. After she came, she didn’t think too much about it. Was it unusual to exclude your own body from your fantasy? Why not, if anything is possible, imagine him loving you as you are? Because (and she knew this absolutely, without ever saying it to herself) her desire depended on her perfection in the eyes of the man.
Jack和Mark是不同的,Mark是她的情慾對象,她與Mark談情時還跟其他男人在電話裡交往;她愛Jack,她因為Jack而不再跟其他男人談電話。但無論在純粹的情慾還是愛,Jelly都陷於自我身分的迷失裡。 她的身分在現實中本身就有雙重性,她認為自己哪裡都不屬於,既不屬於視力健全的人,也不屬於盲人那邊。
Like Ty, she didn’t fully belong in either world, sighted or blind. She was like a character in a myth, doomed to wander between two places, belonging nowhere. That was the word, “belong.” How much she would like to be with someone, and be long—not finite, not ending—with someone.
我想這是作者故意的鋪陳,實際身分的模糊正好與虛擬世界身分的模糊對應。Jelly與男人談電話時,常處於幻想的自己和真實的自己的不斷轉換中。她不只向男人傳播幻想,她也相信自己的幻想,一方面不覺得幻想是謊言,另一方面又為著現實的自己而自卑。現實世界的她以幻想建構自己,但怎樣才算真正的自己?有一點我覺得很有趣—–Jelly問自己,情慾想像可否脫離身體而存在?性本是與自己最親密的事情,性包括我們的身體、意識,某程度上反映人的自我存在,但如果在性裡自己也是模糊的,「我」在性幻想裡變成另一個人跟別人做愛,那麼,自我是怎麼回事?
我看過作者Dana Spiotta的訪問,她說想透過這個故事探討Internet “catfishing” 的現象,網絡上很多人都是con artist,不為錢,而是為愛和關注。虛擬和真實世界交融確是當今世界的現象,連Patrick Modiano在諾獎的致辭也說:「我很好奇,很想知道出生在網絡、手機、電郵和微博的一代代年輕人將用怎樣的文學去表達這個人人都時刻『連在網上』、『社交網絡』傷害到個人隱私的世界,個人隱私在不久前還屬於我們的私人財產,是隱私讓人變得有深度,可以成為小說的一大主題。」(《世界文學》2015年第2期,頁61)作者Dana討論的則是個人隱私的另一面,不是失去隱私,而是透過玩弄隱私製造想像和慾望。Jelly跟Jack說的,有真有假,真的童年片段、某一個真實地址,但假的外貌,假的名字。當Jack問Jelly, What do you look like?Jelly質問自己,到底自己是誰呢?在電話世界裡,我似乎什麼都是,那麼就什麼都不是。
What do I look like? If you look, or if I look? It is different, right? There is no precision in my looking. It is all heat and blurred edges. Abstractions shaped by emotion—that is looking. But he wants an answer.
Jelly got up and went to the mirror. What to do if what you look like is not who you are? If it doesn’t match?
I am not this, this woman. And I am not Lynn-in-the-photograph. Jack must know. Jack knows who I am. I am a window. I am a wish. I am a whisper. I am a jelly doughnut. Sometimes, when my hair falls against my neck and my voice vibrates in my throat, I feel beautiful. When I am on the telephone, I am beautiful.
在真真假假中,自我的身分是如何建構呢?自己建構的想像是我嗎?別人想像中的我是我嗎?還是,真實的我才是我嗎?在現今世代裡,真實的我依賴虛擬世界中的我肯定自己,但虛擬世界的我沒有真實的我去支撐,又是否存在?
這是一個哲學問題,到底「我」是誰呢?「我」的含義比以前的世代更複雜和矛盾。以前眼見為證,耳聽為憑,感官代表真實(當然什麼是真實可以寫一本哲學書),但在現代的通訊世界裡,真實已沒有界線了。Jelly和她的男友們透過聽來建構對方和自己的形象,在互聯絡的時代,就是透過看圖片、影片、面書來認識他人,建構自己,但聽了、看了是否真實?或許,什麼是真實不再重要了,我們只希望不要打破幻想,就如Jelly最後決定給Jack傳上Lynn的照片,好讓甜蜜的時間能多過幾天。
Jelly and Jack是長篇小說的一小部分,沒想到分折出來卻如此完整。我欣賞這篇小說以簡單又日常的情節,嘗試討論深刻的哲學問題。我期待完完整整把小說讀完,看看作者如何處理這個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