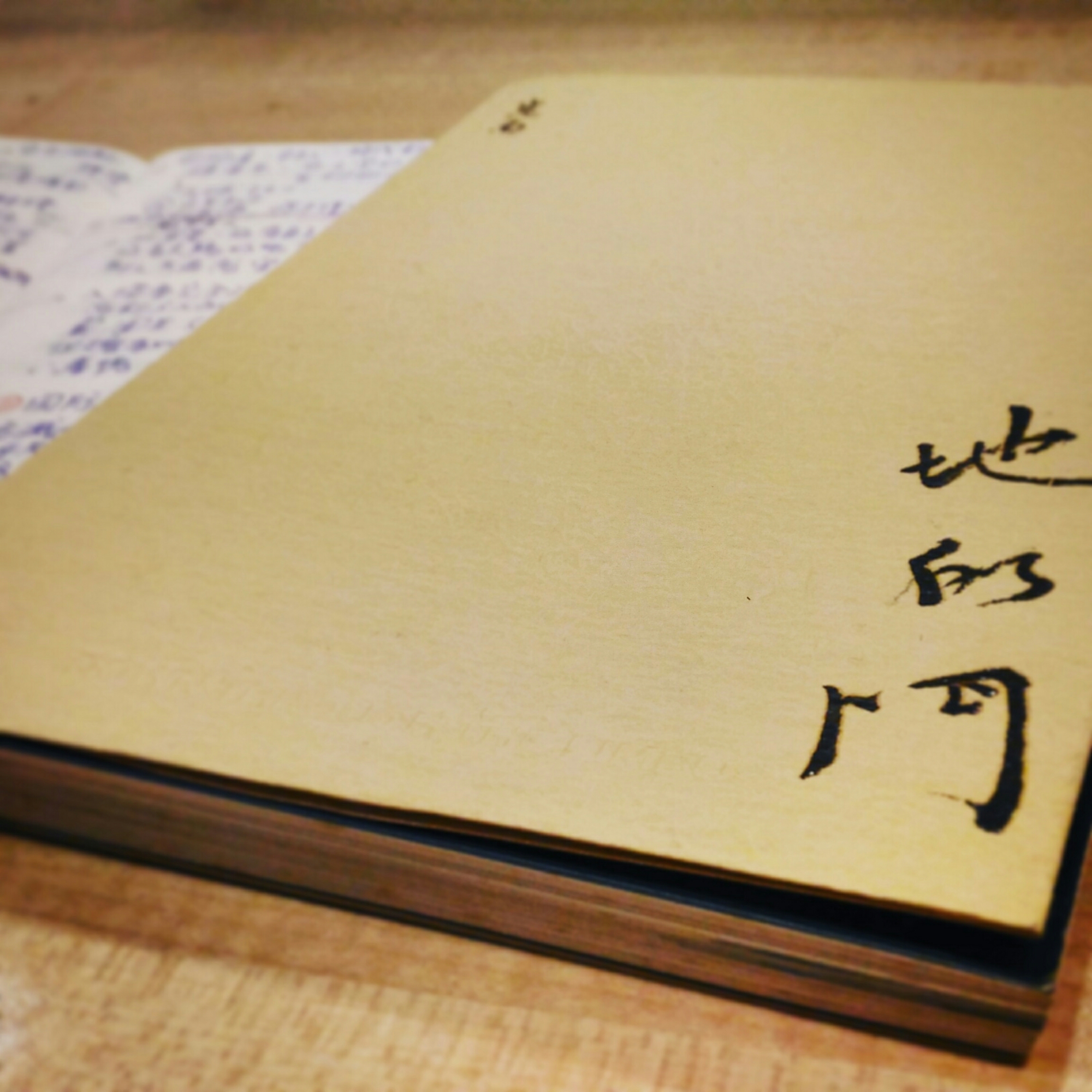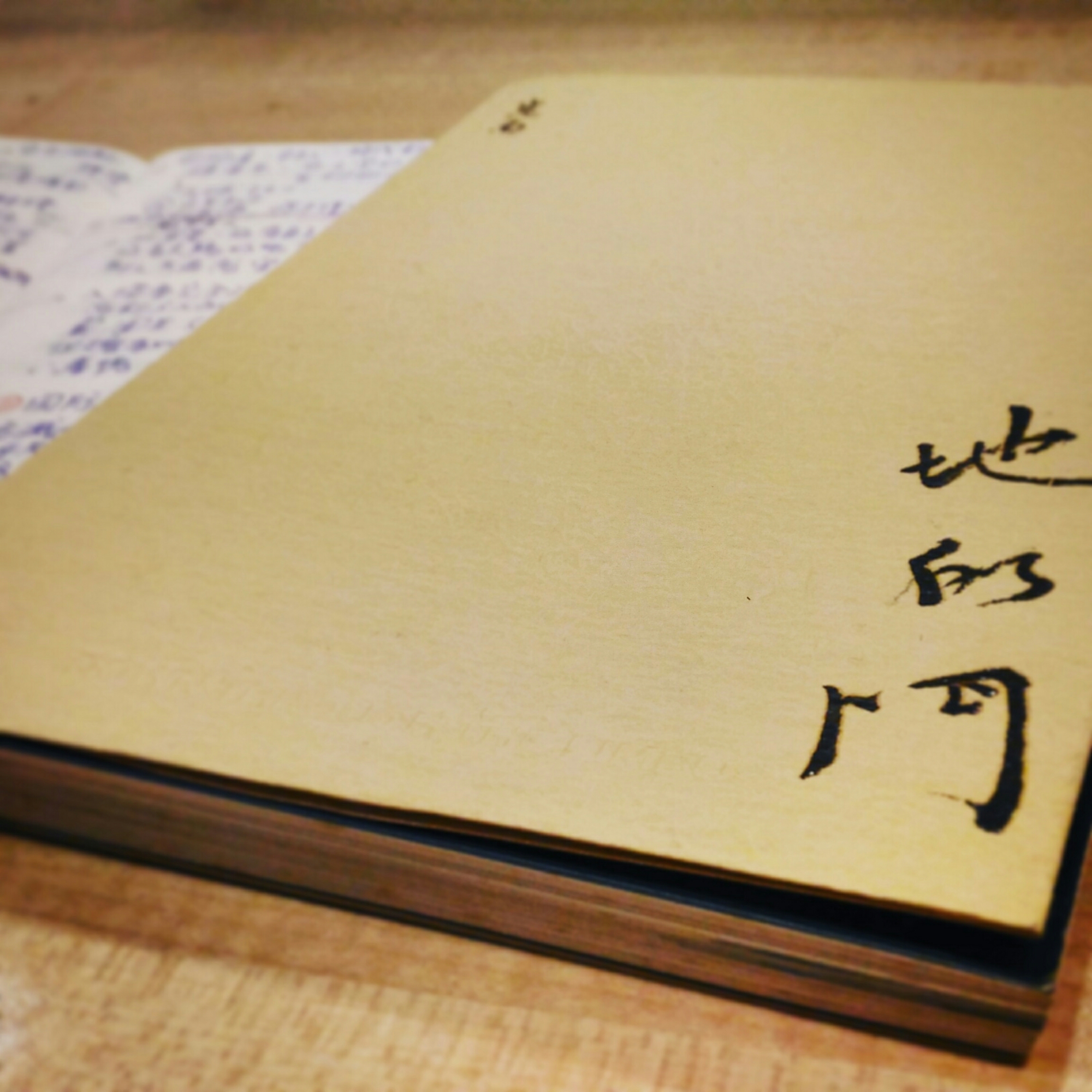
最近有機會與崑南先生見面。我一直追看他的網誌,他認為文學家必須有國際視野、創新技巧和人文關懷,我深深記在腦海裡,雖然仍懵懂不通。早前聽過他的《地的門》,得知最近出了復刻版,我趁這個見面的機會,鼓勵自己把他最有名的小說讀完。
我本身不太喜歡實驗性的小說。《地的門》正是這類型,敘事斷裂、視角轉換,詩、小說、神話,融為一爐。但讀著時我不覺得沉悶,除了想征服這本小說,更多是主角葉文海太像我了--對社會、理想失望,但就算選擇沉淪仍然對理想放不開。
作為普通讀者的好處,就是可隨意把自己的想法讀入小說。我在小說裡讀到精神、慾望和理想三個層面。
葉文海的理想
對主角葉文海而言,理想主要有四方面:
1. 擁有愛情,與心愛的富家小姐雅菁連成一體, 不用理會社會地位高低、家境的懸殊。
2. 不用為了滿足母親和弟弟的期望而做不喜歡的工作,不用背上家庭的重擔,完全做自己。
3. 保持純正,堅持正義,不需為了錢而替殖民地政府服務。
4. 當一個詩人,背負「時代的鼓手」的重任,在文學世界裡找到完全—-「帶我們至到過與未到過的地方。至同一世界裡許多不同的定點。我們將重新經驗已經驗過和未經驗過的經驗。我們常常注意所有現象,有意或無意的。注意它們的發現、發動和衰毀。」(頁60)
5. 世界和平,再沒有衝突。小說中拼貼多段有關戰爭的新聞,葉文海不斷質問,和平是否可能?
葉文海的理想不停留在精神層面,他更希望精神層面在現實世界裡得以落實。雖然他渴望精神層面的愛能解決他與雅菁之間的問題(頁53),但他明白純粹的愛情是沒有力量的(頁56),在現實世界裡不堪一擊。若愛情框在婚姻制度裡,愛就不存在。理想不能為人在現實世界裡帶來救贖,這是葉文海苦悶的原因。
衝突與慾望
小說裡充滿著衝突,衝突源於慾望。慾望,是想控制對方、佔有對方的力量,而葉文海面對他人施於他身上的慾望,總是無能為力:
1. 葉文海和母親經常受大媽媽的兒子欺負,每當葉文海想還擊,媽媽都勸止他,長大後葉文海怪責母親使他變得懦弱,不懂與現實世界反抗。大媽媽的兒子打葉文海,正是受慾望驅使,想獨佔所有人的關注,不讓葉文海在家裡佔一席位。
2. 剛畢業的葉文海應徵收銀員,卻被人騙去一千塊保證金,他無力抵抗。騙子的貪慾把一千元偷去,也把他的理想偷去。
3. 賺錢、爬上高位、愛情裡門當戶對,這些社會意識型態是集體的慾望,重重壓在葉文海身上,把他的自我吞噬。
慾望既來自他人,也源於自己。面對外界慾望的壓迫,理想不能實現,葉文海感到苦悶,選擇沉淪。他的沉淪,就是盡情滿足自己的慾望。他跟隨老張召妓,摟著妓女明明時,他沉浸於慾望,忘記人與人的界線,不只想摸她,還想吻她(頁68)。
明明是葉文海慾望的載體,她在「沒有太陽的地方」沒有表情,沒有愛情。葉文海的慾望使明明認為,眼前的男人與其他男人一樣。由此可見,無論是慾望主體(葉文海),還是被他人慾望壓迫的人(明明),在慾望的桎梏裡,都失去人的獨特性。葉文海跟方葆蓮的愛情跟與明明之間的性形成對比,方葆蓮不是葉文海慾望的載體,也不是施以慾望的人,而是象徵葉文海的理想。方葆蓮和葉文海都視對方是唯一,雙方既擁有對方的身體和靈魂,關係是雙向的。當葉文海被明明拒絕後,他明白到擁有明明的身體但不能了解她的靈魂,就如他了解雅菁的靈魂但不能擁有她的身體,而葉文海的理想是跟方葆連一起時一樣,與對方的身體和靈魂二合為一,想到這裡他感到差愧。(頁69)
作者不讓慾望的衝突停留於個人層面。在葉文海沉淪之時,作者插入大量新聞片段,大部分與美蘇冷戰有關。美國和蘇聯可視為慾望主體,兩個國家不斷擴展自己的慾望,想要侵佔對方的權力和土地。戰爭正正是慾望爭奪戰,人性裡本來就是貪心和自私。兩國吞噬對方的慾望之深,使葉文海質疑世界和平的可能。
慾望的哲學思考
人從出生起就要面對慾望的挑戰,沒有人能倖免。但作者不停在這裡,他要對慾望進行哲學思考,小說後部列出大量佛教經文(頁111-112),我想起以前讀哲學時學過佛教「非分別相」和「分別相」的概念。從佛的眼光看,一切事物源起性空,萬事萬物無所依待,沒有你我他的分別。不執著於事物本來的面貌,是非分別相。而分別相,就是人按其經驗、看法、思考為萬物作區別,人看見自己與他者的不同,執著於不同。如果人能成佛,人看見的世界是圓融為一的,沒有自我,也沒有敵人,我即是他,他即是我,怎會有衝突呢?衝突的源頭,就基於「分別相」,我與他人不同,我要維護我所擁有的,我要滿足我的慾望。
成佛是不可能的,因為人本身有慾望,要滿足自己。成佛是精神層面,但不能解決慾望的不滿足。有時慾望更是超出人的意志,使人不能自由(頁108)。書中羅列出地球不同地層藏有各種動物的化石,人也必然在其中,人是動物之一,在慾望的層面上,人與野獸沒有分別。
但人與野獸始終是不同的,因人有精神,有自主性,人可決定追求理想,還是沉淪於慾望。小說中的「門」正是自主性的體現。如上文所述,葉文海的理想,是靈慾一致。但在現實的壓迫下,人不能實現這種自主性,在現實壓迫下,葉文海只能放棄理想,沉淪慾望,他沒有選擇可言。葉文海說:「就讓自己沉淪好了。一個人不上天的門,便得入地的門,不能在兩者之間徘徊,自討苦吃的。」(頁138)但走入地的門,沉淪於慾望裡,終點卻只有死亡。「從人之子宮裡走出來。不能回到地之子宮裡去。從人之子宮裡走出來。是生。回到子宮裡去。是死。生的門這麼窄小,地的門這麼闊大。」(頁113)
無法化解的孤獨
慾望帶來衝突,衝突引發的,則是無法化解的孤獨。無論是人、歷史或國家,在全球化的世代都無法獨善其身,人與他人、歷史和世界互為影響。即使香港嚴格來說不屬於美蘇陣營;即使此時此刻鴉片戰爭已然過去,世界和歷史仍然在人身上投下陰影。懷抱理想的葉文海,每天生活在歷史和世界的影響下,感到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因而感到孤獨。「葉文海這時好像與世界與香港九龍共同呼吸存在。他不想被任何東西所隔絕,但忽然又想與其他東西隔絕。」(頁76)此外,香港一直缺乏民族意識,在殖民地政府的統治下,歷史被刻意隱沒,葉文海感到上一代不能帶領他走過困境,更感到沒有出路。(頁123)
葉文海多次提到「第三者」,第三者不能控制自己的命運,是微不足道、毫不相干的(頁82)。美蘇對抗時,無數第三者無辜地受波及,受催殘;香港在鴉片戰爭後被迫成為英國殖民地,也是中英戰爭中無辜的第三者。面對命運(或是神),人更是渺小的第三者,葉文海不能與世界與歷史連結,不感到屬於世界和歷史。卡繆說過,人感到自己不屬於世界是荒謬的源頭,荒謬,不就是孤獨嗎?然而,真正使葉文海感到孤獨的,是他對自我存在的自覺。患難是無意義、無標誌的,如果人不自覺;只要生活過得去,滿足口腹之慾,人也可以很快樂。書中拼貼很多廣告的字句,消費彷彿成為孤獨的出路,存在的焦慮被商品麻醉。但葉文海清醒的自覺,既知道純粹的精神不能帶來救贖,又明白純粹肉慾和消費不能化解焦慮,所以找不到出路。
小說末段,葉文海與婷表妹心靈對話後做愛,他第一次體驗到靈慾一致的境界,這是他渴望已久的理想世界。然而婷表妹拒絕與他結婚,他發現地的門與天的門永遠不能融合,連選擇打開地的門還是天的門的自主性也失去,「婷表妹像門留在這個房間,像門消失了。」(頁132),他不願意進入肉慾的空虛快樂裡,又不能打開天的門,最後只能選擇自殺一途。
後記
與崑南先生見面那天,他問我覺得這部寫於五十年代的小說老土嗎?我說一點也不覺得,這不是恭維說話,首先形式上不落俗套,到現在仍然覺得前衛,而且小說不斷重覆的孤獨和焦慮,在2015年的香港仍然深刻。歷史沒有帶來進步,上一代沒有給我們出路,但我比葉文海還好,在充滿無力感的世代裡,仍然有一角色與我連結,有五十年代的苦悶與現今的我對照,孤獨之中不算太孤獨,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