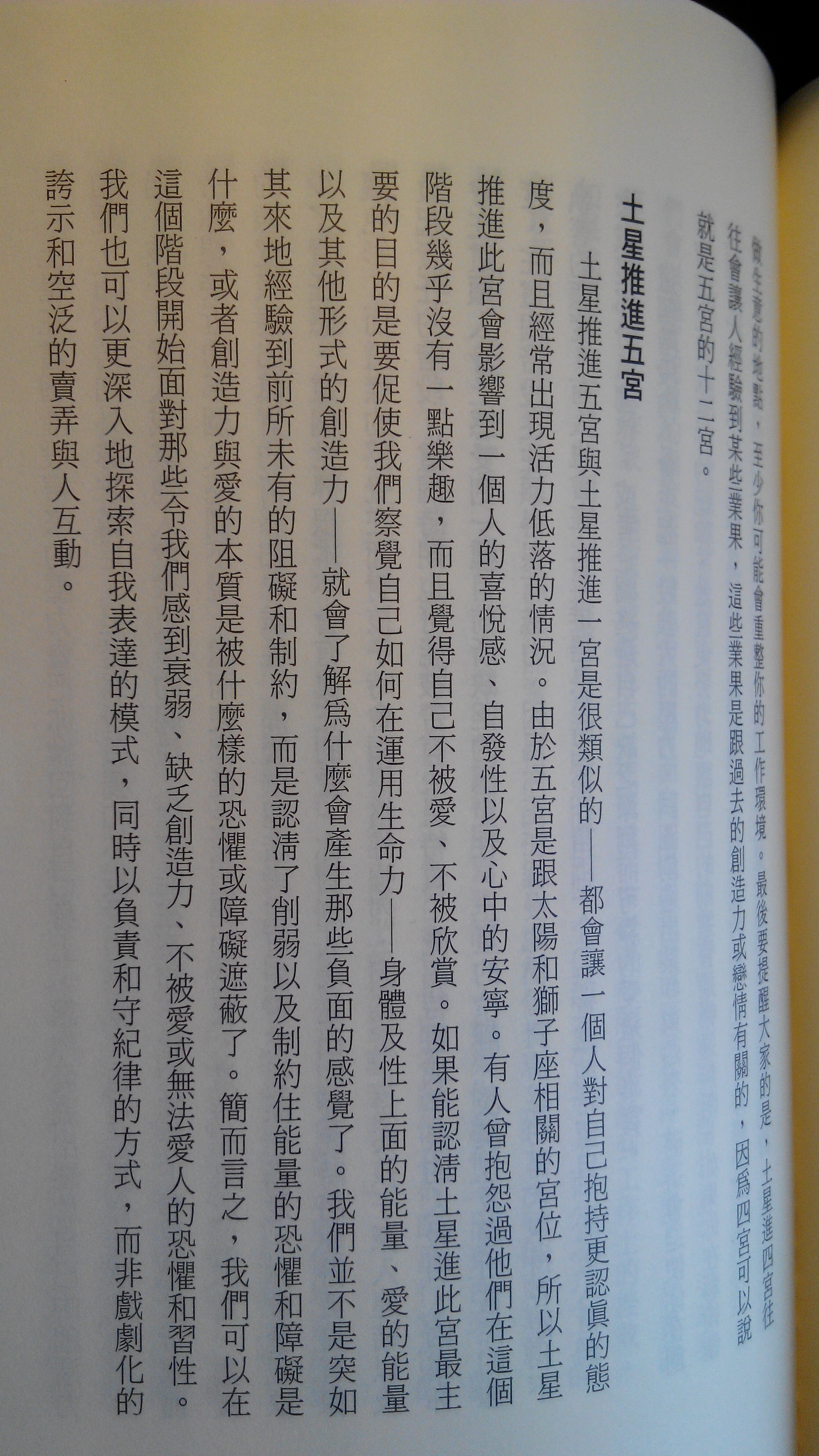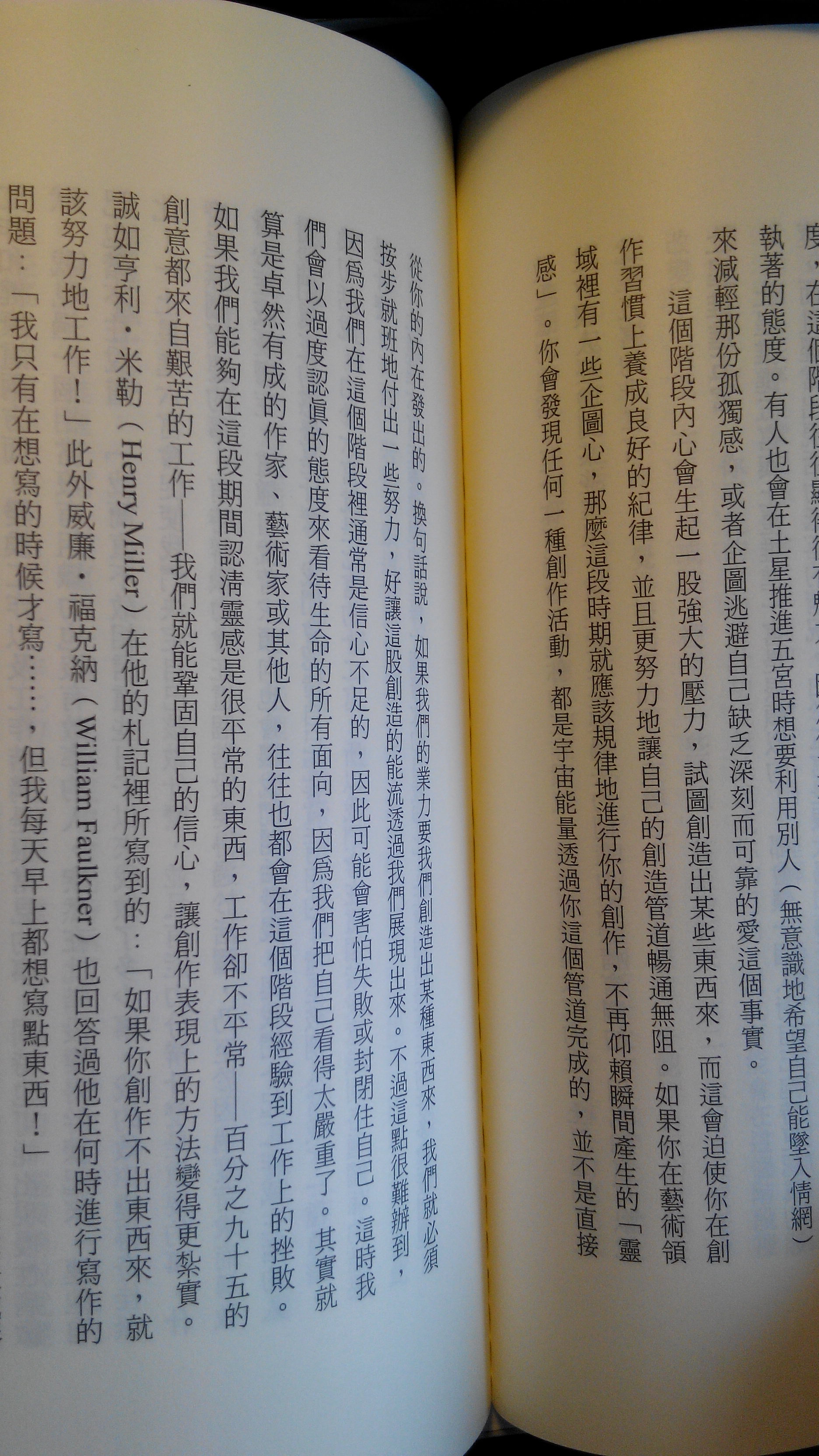很久很久沒有生產自己的文字了。離開編輯的行業,文字如塵,飄落各處,積成厚厚的令人難以忍受的污垢,沖刷不掉。每打一個字都如針刺在皮膚,不完美把我戳得劇痛。文章空洞不能見大雅之堂。到底我愛完美還是愛寫作?
經常有表達自己的慾望,但說到一半就止住。人長大了,到底什麼可說什麼時候要閉嘴,常拿捏不準。很想隨時也向人表白心迹與人交心,但世界太複雜,輕輕相碰也會令人受傷,雖然理智上我知道傷不到我絲毫毛髮。在渴望親密與保護自己之間,我笨拙地保持沉默,以為沉默使我看上去醒目一點,在這個凡事要求精明的社會。
世界紛紛擾擾,而我常常困在生活的苦惱煩瑣裡,泅泳於情緒之海。我想表達對社會的關注,但太怕庸俗,也太怕宏大,害怕偉大的事使我失去了自覺,把別人的口當作自己的口,胡亂搬弄文字,在偉大之下忘記自己只是在假裝。我明白我的懦弱,如果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己」已把我搞得筋疲力盡了;那就把這個自己縮小一點吧,但這個微小的孩子不住呼喊著我,我要一塊一塊磚頭蓋在破碎的生命上,修補很久以前的傷。她的聲音太大,比社會更大。
我卻接受不了自己的自私。我呼喊著,要走出去,走出去。不出去是一個罪名,在這個沸沸揚揚的時代。行動的人才不理會這些小家子氣的感情。個人感受自私得不能與社會連繫,難道一份內疚,一種對自己的不滿,就是不行動的藉口嗎?
心情好時我會接受,我也只能這樣,保護自己不被成長不善而做成的敏感所刮傷。維持情緒穩定是每天最大的功課。我很努力去過我的生活。
但性格決定命運,哪只自己的命運?
最近讀了不少小說,這篇很好那篇也很好,我竟然找不到屬於自己的品味,連自己喜歡什麼都不知道,到底有什麼可寫?連自己最不能失去的事物也察覺不了,有什麼值得我捍衛?
道理上我是知道的。我的頭腦很清醒,內心卻沉睡了。
勇敢地寫一篇不完整的文字,勇敢地面對這個不完美的內心,不完美的自己。從不完美中摸索自己的形狀。像孩子一樣發掘,這個世界於我,到底是什麼的模樣。